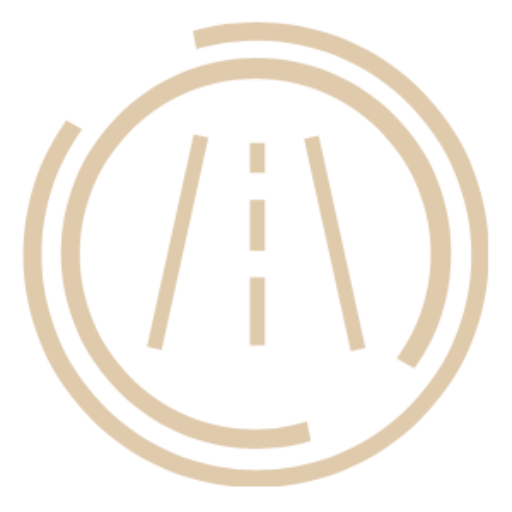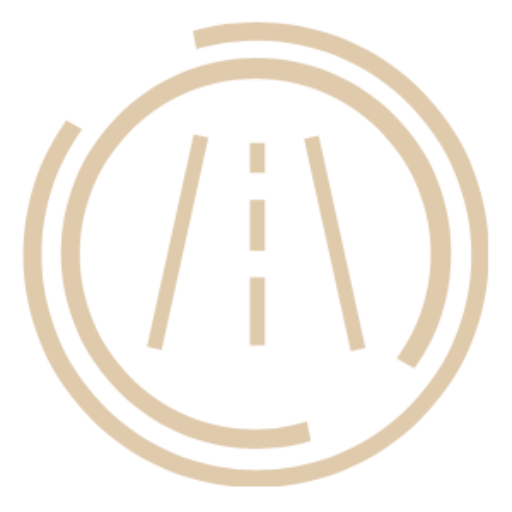我对电影的分类,不是文艺片和商业片,而是“作者电影”和“非作者电影”。作者电影和非作者电影里都有非常文艺的,也有非常商业的。
比如王家卫的是作者电影,就很商业化。非作者电影中也有很文艺的,比如《吉祥如意》。《吉祥如意》是让我对大鹏导演刮目相看的影片。但因为这片子和他其他片子都不一样,明显不是他具有个人风格的表达,所以还不能算作者电影。
作者电影和非作者电影的区别,不在于电影类型,而在于电影与导演的所属关系:电影是导演的,还是导演是电影的;电影是导演主体性的表达,还是导演是电影流水线上的一环。
这就好比一幅画和它的复制品之间的区别。一幅画,无论技术好坏立意高低,就算是三岁小朋友的习作,在它被画下来的那一刻,就具有了画作者的烙印,是专属于ta的、世间独一份的表达。
但复制这幅画,你不需要知道作者是谁,只要有扫描仪和打印机就可以了。复制品,是技术和机器的产物,是一种消除了存在、差异、和生机的状态,它不再活着,但也获得了“永生”(只要持续供应电和纸,理论上可以无限复制)。
因此,“作者”的意义,不是要永远存在,永远活着,而恰恰是在于对必然要消亡这一经验的体察。
一般来说,只有对作者电影,才谈得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可以说喜欢莫奈的睡莲,但没人说喜欢睡莲的明信片和冰箱贴。而我讨厌王家卫的电影,但那些王家卫的“赝品”们,是根本连被讨厌的资格都没有。
作者电影和非作者电影的另一个区别,就是只有作者电影才具有艺术创作的可能性。这个很容易理解的,艺术成立的前提条件一定是具有主体性的创作,也就是说它首先是一个活人的表达,仅仅是机器无意识的运动产生的东西,即便它再精美也不能叫艺术。如果一个主体性的创作还能够探索和扩展感官和认知的边界,并由此创生和滋养众多其他主体性的表达,那它就可以被称之为艺术了。
因此,卓越艺术的首要属性,是探索性和先驱性,而不是样子美不美,技艺高不高,人们能不能欣赏得来。
很多艺术作品在它产生的当下是不被欣赏的,但它确实探索和表达了一个大多数人还未能到达的维度、视角、或天地,在ta这样表达之后人们才开始这样看世界。
比如安迪霍尔的鸡汤罐头系列,它本身说不上美不美,但它确实打开了一个新的视角,模糊了高尚与通俗、严肃与戏虐、精英与草根之间的界限。在它之后,涌现了一大批的创作和表达,开始以新的视角审视现代生活。能做到这点当然算是艺术。
流水线工业中的电影,是符合现代工业标准流程运作出来的可交付的项目,它本质上和任何工业车间制作的产品毫无二致。首先是资本给了预算和利润要求,然后根据市场调研、用户需求做项目规划,再按照消费者的偏好设计剧情、台词、反转。目的是为了把这东西卖出去,提高票房,赚取利润。在这个过程中,导演不过是流水线上的一环,你肯定不会说组装零件的负责人就是“作者”吧,这样出产的电影导演也同样不能算作者,最多算个project manager。
不要误会,我说这些不是要为这部《狂野时代》辩护,啰嗦什么这是作者电影所以你们看不懂的陈腔滥调。
毕赣肯定是作者,他的电影也一定是作者电影,这无容置疑,无需辩护。我说这些,是因为这个“主体性的表达、探索、和体验”,恰恰就是这部电影的主旨。《狂野时代》讲的就是这个东西。如果说辩护,那么电影本身就在给自己辩护,本身就是解释自己的注脚。
“在一个狂野的时代,人们发现了永生的奥秘,那就是不再做梦。人不做梦就如同蜡蚀不再燃烧,便能永恒存在。偷偷做梦的人被称为‘迷魂者’。他们让现实痛苦、历史混乱、时间痉挛。”
这段导演对观众所说的话,其实就是我前面所说的“有生命的注定消亡,没有生命反得永生”的悖论。在这里,很显然,永生不是正面的,消亡也不是负面的。甚至痛苦、混乱、痉挛也不是负面的。
人们太容易拥抱二元论,也太急于划分好和坏的阵营。好和坏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放诸四海皆准。判定好坏,是人为了生存所做出的必要的妥协。就像我们的眼睛只能识别可见光,那是因为我们处理不了其他的光。我们只能看到可见的,但这不代表看不见的东西就不存在。
好与坏的设定也远非事情的真相。真相更像是一种悖论,你以为矛盾的,很可能只是超越了你的认知,你看为有损的,可能对你有益;你孜孜以求的,也许虚妄;你一心想要抛弃的,很可能是最宝贵的。
做梦,实际上就是欲望。活着的人就会有欲望,有欲望代表人活着,人活着代表有一天会死去,但人都不想死。所以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渴望,人便一股脑儿的同时厌弃了生命和欲望。
你看懂这层逻辑了吗?于是乎,人经常会在道德的层面上谴责生命力旺盛和欲望强烈的行为和表达。生命力越旺盛,他们所感到的死亡也就越逼近。禁欲,是对生命的否定,同时也是对永生的渴望。这又是一个悖论:禁欲实际上是另一种更强烈的欲望的表达。因此,无论人多么急于否认,他都逃离不了欲望,就如同你不可能不做梦,不可能不渴望什么,不可能逃离死亡一样。
永生的奥秘,就是死亡。人不死,就无法永生。这如此矛盾,却又如此和谐!
“迷魂者”执着于做梦,无非是想要去体验活着的感觉,活着的感觉无法在永生中体验,有限的感觉无法在无限中体验,这道理如此简单,以至于你都忘了:你活着,并活在一个有限的处境中,这其实就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你就是为了要经验那在永生和无限中无法经验的东西——痛苦、混乱、痉挛、死亡——而来到世间。苦妖为什么要为尝这个苦而伫立千年?因为没有苦,甜又有什么意义?
毕赣用“色声香味触”五相来构建一个“狂野时代”,既是感官世界的表征,又是人类有限的表征。在这样一个“狂野的时代”,“着相”确实带来了痛苦和混乱。五个分别代表“色声香味触”的故事发生在不同的年代,全部以死亡告终,色调阴霾,黑夜笼罩、在下雨或下雪,在某个阴暗的角落,人在社会的边缘游走,生命被打压、霸凌、伤害、和消除是五个故事的主旋律。
毕赣似乎刻画了五个悲剧,但又不同于佛教和基督教对苦难的态度。前者对这个世界是怜悯,后者对这个世界是定罪。而无论怜悯还是定罪,信徒们都急切地想要将人“救”出这个世界。
单看这五个故事,似乎很符合佛教或基督教的语境。但毕赣在影片的开头,使用了一个小技巧,就是打破第四堵墙,让火把屏幕烧开(让我想起《小品的世界》里吕严奋力锤墙的桥段),再让“大她者”将摄像机对准观众。这样一来,观众必然会意识到,你在看戏,同时你也是戏中人;你看的是故事,你的人生又何尝不是故事,有很多的“大她者”要救你出去,但经验这一切,又何尝不是你主动的选择?
“着相”其实未必是一个牢笼。有人仅仅因为电影中出现了很多古早影片的影子,就认为这是导演写给电影的情书。实际上,电影和情书都是载体,上面承载的,是导演写给人类的情话。
电影是他熟悉的表达手段,也是他欲望的出口,但电影作为工具本身没什么可致敬的,甚至它作为机械化的产物一度是丑陋的,正如“迷魂者”最初和末了的形态。但借助这个丑陋的躯壳,却演绎出了无数动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强加于“迷魂者”身上的,而是ta,是你和我,主动进入的。是的,我们都是“迷魂者”,我们都主动选择构建了我们自己的人生,以及我们自己的故事。
“大她者”在我看来,是一个天使的视角。ta不等同于上帝,ta搞不懂为什么有的主体义无反顾的跳入人生苦海,ta一边帮他们完成梦境,一边在旁观察:这个星球上又苦又累又痛又伤的轮回,到底有什么迷人之处,让人置永生而不顾,甘愿为之焚烧殆尽。ta肯定无法找到答案,因为只有自己投身苦海,才能得尝苦海之甘。
我们都是戏中人,我们也都是看戏的人。这是电影赐予我们的特权,我们可以如“大她者”那样观看他人的人生, 你可以喜欢或讨厌这五个故事,正如你可以喜欢或讨厌自己的人生。没所谓的。因为你知道吗,对于“大她者”来说,ta们甚至没办法讨厌或喜欢什么,因为只有你置身于那种有限的处境,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上帝视角只能透过感官去认知世界的时候,才会经验那种五味杂陈、苦尽甘来的情绪。别说“大她者”,就是活了很久看透了很多的人类,也会发现自己已经没有年轻时那么激烈的情绪了。
但有情绪不是坏事,欲望不是坏事,生而为人也不是坏事。虽然它们带来痛苦、混乱、和痉挛,但正是这种经验,可以让精神苏醒,让灵魂复活。
电影的五个故事,可以看作是一个灵魂在这感官世界的五层轮回,五次重生。
第一层,是“色相”。妓院和大烟馆是色的极致体现,眼目的情欲终结于直面丑陋的那一刻。“大她者”用红色的幕布遮起“迷魂者”,在ta的背后装上胶片,“迷魂者”丑陋的面貌在红色的幕布前,化身电影院里的放映机,从这里,“迷魂者”得以进入后面的梦境。
第二层,是“声相”。声带来混乱和迷失。声音就是频率,而人的生命就是频率。脉搏是频率,心跳是频率,呼吸是频率,生命的根源在于频率。因此声音可以最直接的触动人的心弦,也可以最猛烈的夺取人的心智。迷魂者在“声”的世界因为声被崇拜和迷恋,也因为声被伤害和撕毁。
第三层,是味觉。味觉的故事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苦妖,苦妖是所有人物中最为灵动的。苦妖专为尝苦而来,但他发现最苦的,不是那泡尿带来的苦味,而是人心中的悔恨。离佛只差一步,看透了苦就能成佛,看不透,就如同迷魂者一样,化身黑犬,惶惶不可终日。
第四层,是嗅觉。人的嗅觉直通心灵。大脑记不住的,鼻子可以记住。你闻到熟悉的味道,可以唤起心底深处的记忆。嗅觉是人身上的特异功能,并不需要特别训练。迷魂者成为混迹街头的骗子,利用小女孩的嗅觉去骗钱,却无意中让被骗的和骗人的都获得了一丝丝的安宁。
第五层,是触觉。迷魂者爱上了吸血鬼女孩,还有什么比吸血鬼之吻来得更深刻的触觉?如果有,那一定是第一缕阳光照在吸血鬼身上,皮肤开始灼烧的感觉。这一次,迷魂者的情绪最为愉悦,虽然爱欲带来追逐、焦虑、迷失、和暴力,但最终,他们还是赶上了新世纪的日出,而这一次的日出也将他的肉身彻底烧尽。
蜡烛越烧越短,火焰越来越微弱,死亡将至。”大她者“为”迷魂者“重新装扮成最初的丑陋模样。在天使看来,人类的躯体本就是丑陋的不是吗?
这样的沉重,这样的粗鄙,这样的污浊。但轻盈、光明、绝对理性如大她者,无论如何不能明白,在这沉重肉身的躯壳内,有怎样丰盈、有趣、充满生机的体验。梦想和欲望,是上帝为非永生者所预备的礼物,是让人一次又一次复活在下一个梦境中的火种。
这就是我在《狂野时代》中所看到的。其实我看懂的,是我想看到的。你看懂的,是你想看到的。本没什么标准答案。你说你看不懂,不是你不懂,而是这里暂时没有你想要的。你把这些东西存在心里,它们会在适当的时刻醒来,到那时,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