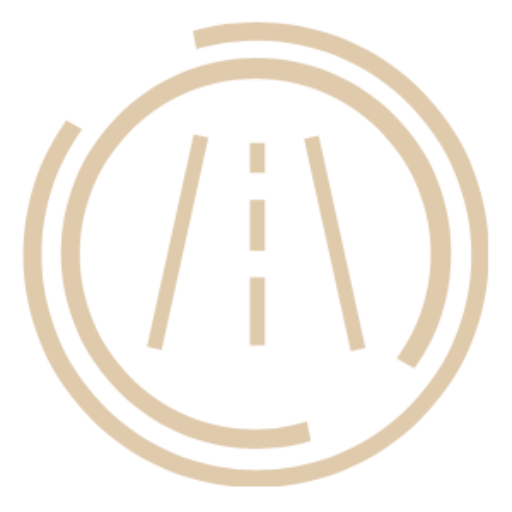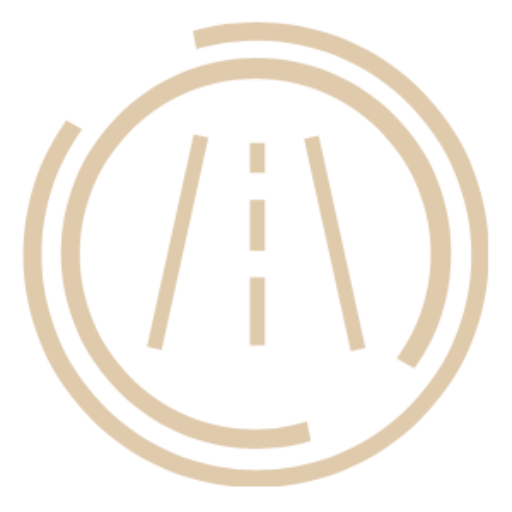首先要知道一件事,当我们说某个哲学家反基督教的时候,实际上ta反对的是那个时代和语境下的基督教。
这道理很简单,任何批判、观点都是概念的衍生,而“概念”这东西并非一成不变、也不是千人一面。
比如你发现了一本几百年前的“铁匠入门”,肯定不能照搬里面的内容炼铁,现在的物质条件和过去的物质条件不一样,或者说升级了。很显然这本“手册”不能指导你今天的工作,但通过它,你可以了解那个时代。
神/哲学也是如此 。神学教义和宗教实践一直在演变,从最初的犹太教到使徒时代、从尼禄大逼迫到罗马国教、从教父时代到启蒙运动、从理性至上到奥斯维辛之后的悲悯和人文转向。
每个时代的神/哲学家都在回应ta那个时代的问题,他们写下那些东西,是为了引导那个时代的人类前行的脚步。
当今的时代有当今的问题,条件不一样,机遇不一样,问题也不一样。
我们有义务回应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前人的答案不是为了指导现在的你,它们最重要的功用,是让你通过它们了解一种思想和认知是怎么发展到今天的,
——什么被历史淘汰了,什么塑造了历史,什么结束了,什么开启了。
尼采回应的也是他那个时代的问题。
你读尼采(其他哲学家也一样),要把他放在19世纪启蒙运动和产业革命下的欧洲来读,放在那个路德派的家庭背景下来读。然后要读圣经、读那个年代的历史,读他同时代神学家的神学。
他写的都是对这些的回应,你不熟悉这些,很容易代入你熟悉的现代经验和概念,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是在说那个,而是有非常具体的所指。
我们今天活在后奥斯维辛时代,这个时代的神学特色就是“人性化的上帝”。这个“上帝”与尼采时代的“上帝”截然不同。
尼采或者说启蒙时代的上帝是“超越的上帝”,祂超越人间疾苦、超越人类经验、超越人类理性、不接受人类质询和拷问。
在“超越的上帝”框架下,很多东西你无法追究,或者禁止你去追究,比如“道德”、“理性”。
因为那就是一种设定,是上帝赋予的,如同“上帝”不接受质询,“道德”和“理性”也就具有了本体论和目的论上的意义,也必然是本质的、普世的、不容置疑的。
【插一句:很多人对这种哲学术语比较陌生。简单说就是对事物的定性。好比你断言,”一个人生下来就是个好人,就是为了做好人而存在“。把这个“人”换成其他事物,就是在讨论ta的本体和目的了。用这种方法讨论事物,会出现两个后果,一是它从此拒绝任何其他判断,二是它是timeless的,不会随着时间和历史而改变。
给事物定性其实从柏拉图就开始了,基督教只不过以上帝的名义来做这件事。但和希腊哲学圈不同的是,教会的权威太大了,它所做出的判断和决定已经远远超出了一小撮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教会本身的范围,变成放之四海皆准、超越历史和经验的教条。
这就是“基督教美德“所带来的问题。无论是做慈善也好、禁欲修行也好,都变成了自有永有、理所当然、亘古不变的”公理“,没有人敢问、敢想,它们是不是、仅仅、就是人的传统?】
“超越的上帝”在二战以后开始式微,因为它无法回应奥斯维辛的经验。
人类在受苦的时候,上帝在哪里?理性在哪里?道德在哪里?这些问题,高高在上的上帝无法回答,唯有十字架上的“子”,借着祂的牺牲与原谅,可以回应这个问题。
理性和道德不是上帝的标志,爱才是。
但这是后话了。在尼采那个年代,还没有世界大战,还没发生奥斯维辛,殖民主义还没瓦解。人类尚不需要一个“共情的上帝”体贴和接纳他们的软弱和破碎,他们相信上帝赐予的理性和道德会持续将他们带向更高更远的佳美之处。
但尼采显然对此没那么乐观,也许是自身的经历,也许是天生的敏感,他不像同时代人那么毫不怀疑地拥抱理性和道德,特别是道德。
可是刚才说了,那个年代,道德是和基督教美德捆绑的,基督教美德又是和上帝捆绑的,它们具有本体论和目的论上的地位,是人不得不相信、不得不服从的东西。
教会除了推崇三圣愿——贞洁、服从、安贫,还有信心、自卑、怜悯、禁欲、苦行等等。你是个信徒,就得具备这些美德。丧失了基督教美德,你就要受良心的谴责、教会的刑罚、以及将来的审判。
这些都是尼采在他那个年代自身经历最深刻的东西,也是他反弹、批评最厉害的地方。
我们大多数人没有这些经验,你很难想象教会长大的孩子身上背负多大的重担。你做错事,不仅严刑拷打,还会告诉你地狱的火等着吞灭你,天天晚上做噩梦,这是很多人的青春期。
这些人长大以后内化了这些认知,继续传递给下一代。而尼采跟他们不同的是,他提了个问题,道德是什么?
道德不就是上帝吗?他们说。
但尼采说,道德是“历史、社会、和文化的产物”。而”美德“,很可能就是个传统。
教会强行教化基督教美德既不符合人类的真实生活经验,也不有助于让人变得更好。
具体来说,是教会绑架了人类真实经验,人为地高举一些奉为美德,贬低另一些斥为卑劣。所谓“美德”,不过是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对立和博弈的结果。
比如“好”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形容词实际上一开始都是贵族对自己的描绘,比如“noble”本身就是贵族的意思。而“坏”的概念,比如“malus“表示邪恶,最初指的就是黑头发黑皮肤的人。
这就是“道德谱系学”——对道德追根溯源——所要做的事情,也是尼采批评“怜悯”等基督教美德的语境。
其实对于今天的人来说,对任何概念都该追根溯源,在合适的语境中去理解,这没什么新鲜的,属于正常的研究思路。
但在尼采以前,把“道德”这种神圣的概念历史化、相对化、处境化,实属大逆不道。
想想看,整个基督教都是建立在人“生而有罪”的基础上,你说“罪”不是始祖吃了禁果,而是生物学、社会化、心理学的产物,基督教大厦要垮一大半。所以尼采反对基督教,首要的任务就是反对基督教美德。他认为当基督教美德失去本体论和目的论地位的时候,基督教这个宗教就垮了。(但事实是,这些概念失去本体论地位的时候基督信仰并没有垮,详见《Bible女性系列的夏娃篇》)
不过尼采虽然反对基督教,但却深爱耶稣。
他看不上的是保罗。因为耶稣亲身示范了爱,结果被保罗硬生生搞出个赎罪的宗教,衍生出一大套基督教美德来换取救赎。
所以才有那句振聋发聩的——“上帝死了”。
“上帝死了”,第一次被你们钉在十字架上杀死了。第二次被你们绑架在宗教的桎梏中杀死了。
“上帝死了”,因为你们用僵化的教条取代真理、用使人恐惧的定罪和刑罚取代仁爱、用虚假的权威取代真正的权柄。
“上帝死了”,是“宗教的上帝”死了,好叫“真实的上帝”活过来。
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就可以谈谈尼采所批评的“美德”了。
尼采所批评的“美德”,必须是作为基督教美德的“制度化的美德”。
他批评了善与恶、好与坏、罪恶与良心、禁欲主义等其他基督教伦理和实践,但其实不是否定这些美德本身的价值,而是在这些教义成为教条的过程中,人实践这些美德,并非出自本心,而是出自压力、威慑、恐惧、虚荣、傲慢等与美德无关的东西。
因此他要回到这些观念产生的最初,对他们作出谱系学的挖掘,探究他们的根源,不是在所谓的神圣的启示中,而是在社会的教养和人类心灵的软弱中(就是现今的社会学和心理学)。
上面讲了“好”与“坏”的例子,他分析了这些词语的源头。对于“怜悯”,他也作了分析。
但老实说,这个分析基本上接近于胡说八道,我觉得完全没有细说的必要。比如他说同情是弱者腐化强者的手段。弱者之所以同情是因为介意他人的眼光,或者“报复”之前强者相对于ta的优势。云云。当然也可以联系一下“奴隶道德”的概念,但即便如此也是牵强附会。其实“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的论述本身就很扯。
不要误会,这不是贬低尼采。
他的分析也许矫枉过正,但分析本身准确与否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他动摇了基督教美德本体论和目的论的地位。
——有人,居然,敢,质疑基督教美德不是上帝的设定。
如果不是上帝的设定,教会又凭什么强行绑架信徒?凭什么咒诅和惩罚“道德”不达标的人?
格局这不是一下子打开了吗。
所以其实一开始我就说了,所有思想家/发明家的伟大,在于开创一个新的时代,而不在于他们那套东西还适用。
莱特兄弟的飞机现在还有人用吗?但就是从那时起,人类离地面越来越远,离天空越来越近,直到有一天飞出这个地球。
尼采也是如此,虽然他的理论笨拙,但他开创的时代,是把宗教覆盖在人类头顶上的乌云驱散。
——那乌云就是各种假以上帝之名制造的传统、教义、道德绑架以及刑罚的咒诅。注意,这不仅限基督教。
虽然今天还存在这些东西,但它们的根基已经松动了。
比如神学家们不再害怕用形而上以外的视角研究神学。比如就算平信徒查经,处境化和语境化的解经也已经成为主流。比如我们此刻就生活在尼采所开创的时代,以尼采所开创的方法思考、判断、解决问题,回应现在教会面临的挑战。洪亮老师说的“尼采是基督徒的同路人”,我是举双手赞同的。
这才是尼采重要的地方,也是今天阅读尼采的意义。
下面张经纬说的这段话,可以用来结束今天的文章:
时代在变,诸子百家的思想不必以“经典”的形式成为后人行为的标尺,乃至思维的束缚或桎梏。我们要把自己从历史的束缚中释放出来,而不是把老祖宗的每一句都当作不可违背的金科玉律,我认为这是研究传统文化的意义。我们应该回到那些思想的源头,重新发觉它的含义,引发自己的思考,启示今天的生活。
(张经纬《诸子与诸国》)
尼采的话,不是他说对了什么,而是他指出来,这个世界还可以这么看,于是听了这话的人,这么一看,世界果然就不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