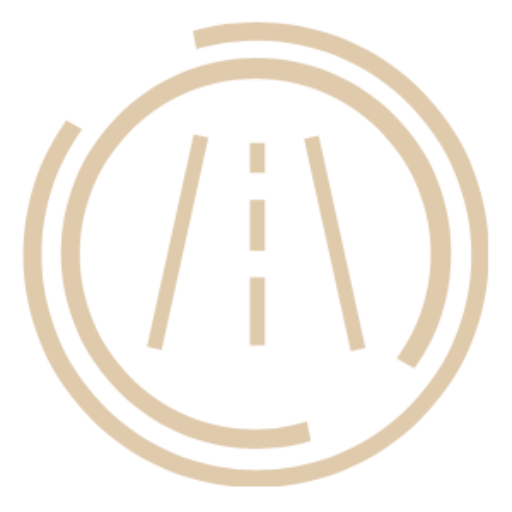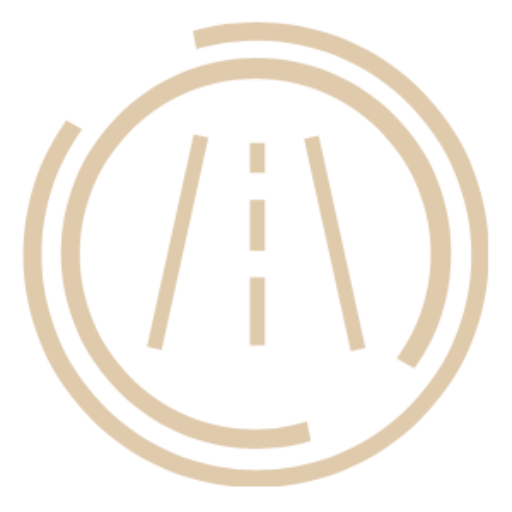我之前写过两篇主要从信仰和宗教方面来谈以色列在巴以冲突中的责任。这篇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也讲“巴以冲突的由来”。
历史
“以色列”最早出现在《旧约》以外的历史文献中,是1896年发现的埃及Merneptah 法老的石碑。石碑记载了法老公元前1209年出兵迦南,打赢了迦南城邦和“海上民族”的事。其中提到了“以色列”。
但值得注意的是,依照埃及文字的写法,迦南城邦的后缀代表“国家”,“以色列”的后缀代表“民族”。也就是说,在埃及人看来,当时的以色列还不足以称之为“国”,它很可能是还散居在中央山地尚未建立城邦但已具有某种民族认同的一支或几支部落。
公元前13世纪末,具有“以色列”民族特征的部落联盟出现在巴勒斯坦中央山地一带。上一篇回答讨论了最早的以色列人到底是谁。这里长话短说,主流观点认为他们就是迦南人,但因为不满迦南统治来到山地定居,可能也有来自两河流域的游牧民族,和从埃及辗转而来的精英领袖,这些人带来了他们各自的集体记忆,有游牧的,有出埃及的,有征服迦南的。但最核心的、也是牢牢把他们凝聚在一起的,是对迦南文化的厌弃和抵抗[1]。这时,“以色列”还没有王,但已成为了一支足以令埃及人注意到的政治和军事力量。
到了公元前11世纪,“以色列”在北部,“犹大”在南部分别建国[2],“以色列”定都撒玛利亚,“犹大”定都耶路撒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色列”比“犹大”更强大。1868年出土的Mesha石碑记载了公元前9世纪以色列曾占领摩押土地多年。这说明至少在9世纪以前,“以色列”就已具备了征服和奴役周边国家的实力。而南面的“耶路撒冷”,至少到8世纪前,都只是一个只有几百人的小村落。
公元前722年,“以色列”为亚述所灭。大量“以色列人”涌入犹大,这才使得政治和文化中心转到南国,耶路撒冷也从一个几百人的村落迅速发展为几千人的都市。
逃亡到犹大的以色列人在犹大王希西家的带领下,和犹大人一同完成了一系列宗教和政治改革,完善了一神教信仰,编撰了律法,建立起了以以色列/犹大为叙事主体的民族和宗教史观,理论上完成了”以色列“民族的统一。
说“理论上”,是因为在实践中,民族(nation)的构建是需要有一些历史条件的,大部分古代人其实都是生活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以色列”民族真正建构起来,是在亡国之后。
犹大公元前586年为巴比伦所灭,当时被迁徙到巴比伦的居民还是以“犹大人”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居。《以斯帖记》讲的是波斯年间的事,我没记错的话,里面通篇说的都是犹大人,一个字没提以色列。即便主人公是北国以色列后裔,也自称是犹大人,而不是以色列。
如此说来,以色列的民族认同是怎么形成的?
应该恰恰是得益于以色列/犹大居民被迁徙到各处离乡背井的经历。被迫放弃家园的人一般就两种选择,一种是遗忘,一种是记住。以色列选择了“记住”。
为了记住他们是谁,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流散的以色列人特别致力于打造社区和家庭教育。以色列人的识字率一直比周围的民族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需要识字的人翻译、诵读、传讲圣经,一个家庭或社区的领袖有义务自己研读圣经并教导民众和家人遵守。不同社区的以色列人还通过信件的方式传播经书和律法。经书告诉了以色列人他们是谁,祖先是谁,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律法告诉了他们要如何度日,如何行事为人,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如何在逆境中生存下来。
因此,虽然早在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就流散各处,但正是在流散中,以色列的民族认同才算真正建立起来。这比欧洲早了一千年,如果中国的民族自觉(有了“人民”的概念)以周朝来算,那么大抵是东周这个时期,以色列人也获得了民族自觉。
“以色列”的民族自觉,伴随着,或者更准确的说,扎根于它们失败、亡国和没有家园的经验。只有认识这点,你才能读懂《旧约》中所体现出来的神学观和世界观。也才能明白为什么有一部分犹太人死也不要建国的思维逻辑。
公元70年,犹太战争失败,第二圣殿被毁。公元135年,犹太人再次集结起来反抗罗马,再次失败。从此,犹太人被驱逐,耶路撒冷被改名,迦南成为叙利亚巴勒斯坦,并禁止犹太人进入。
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巴勒斯坦的居民有90%巴勒斯坦人,10%犹太人。现代基因研究证实这些本地人身上有一半迦南人基因,另一半来自于阿拉伯、北非(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德法及东欧国家(巴勒斯坦犹太人)。
是的,巴勒斯坦土地上一直有犹太人的身影。
但如果说以色列一直是巴勒斯坦的主人就不正确了。
以色列/犹大从建国到亡国,分别是300和400年,之后分散到各地的犹太人就超过了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即便把后面的马加比王朝算上,也不到100年。公元70年罗马人驱逐犹太人,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就更少了。
而在这之后差不多一千年里,都是本地迦南人居住在那里,只不过他们没有保留最初的民族性,逐渐与外来的统治者特别是阿拉伯人、突厥人融合了。原先他们叫迦南人,现在他们叫巴勒斯坦人。但即便如此,他们身上也携带着一半的迦南基因。但他们与犹太人不一样的是,他们并没有离开自己的家园。
以色列的“民族”意识形态
公元70年到19世纪末,主导以色列的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民族超越国家的意识形态。
这种意识形态也是对《旧约》神学观和世界观的反映与折射。
上文我们提到埃及法老的石碑和摩亚王的Mesha石碑,对比这些帝国或君王叙事,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推崇的历史观跟它们都不一样。
第一,石碑与信纸。
在近东地区,立碑是帝王记载自己丰功伟业最直接的手段。原因很简单,这不仅代表了他个人的伟业,也代表了他统治的疆域。
他们立下石碑,以为可以流传千古,殊不知这样的傲慢在历史和时间的流逝中非常脆弱。碑石的坚硬和宏伟也意味着僵化和缺乏机动性,当帝国更新换代的时候,王可以逃走,但石碑搬不走,最后只好被人打碎或封印在博物馆里。
相比带不走的石碑,柔软的信件就更方便传播了。当然,石碑和信件的功用也不一样。立碑是为了君主的威严,而信件的传播是为了汇聚记忆,建立信念。
古代帝王一直以为,百年基业依赖于帝王将相,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民族的延续实际上依赖于人民,依赖每一位子孙后代,依赖无论走到何方都可以把他们的祖先叙事传递下去的人。
所以那些建立在石碑上的帝国,被征服了就消亡了。而那些建立在书信上的民族,即便被征服,也可以在世界各个角落存活下来。
第二,英雄叙事和人民叙事。
旧约中的战争和征服几乎全部以第三人称写作,而石碑叙事几乎全部以第一人称写作。
石碑对战争的描述、对征服的理解、以及对君王自身的弘扬无疑是君王视角,或者说是“英雄叙事”。凸显的是作为天选之君的主角光环,个人主义和英雄主义,完全不会关注和提及民众的情感和经验。它所要达到的情感回应是百姓的畏惧和服从。
《旧约》中战争的主角虽然也是君王,但你如果仔细读,就会发现这些“主角”都没有主角光环,取而代之的是第三方的审视和批判。比如在历代志和列王纪中多次出现的,“在祂眼中视为善”,“在祂眼中视为恶”,“祂喜悦这事”,“祂厌恶这事”这样的判语。其中颇多是以上帝的口吻站在人民的立场谴责以色列的领袖。
然后,君王也不总是赢。更准确的说,是输多赢少。
那么为什么要记录这些败仗?那是因为失败比得胜更能教给子孙后代生存的智慧。
以色列的史书是以失败而非胜利结尾的,当然这一方面是客观事实,但另一方面,是这失败的痛击可以不断地提醒以色列的子子孙孙,他们的民族身份和处世之道。
第三,王权和民权。
之前说过,以色列先知在”先知书卷“中对君王、富人的批判是超越年代的,这可以被当作上帝公义的象征,但最直接的,是因为这些书卷的书写和编撰本身就是在一个王权衰败的背景下完成的,以至于书写者并没有畏惧王权的禁忌,反而是充满了对君王的失望和愤怒,以及对人民的同情和怜悯。
这里的”人民“甚至是超越种族、民族和阶级的。
比如”摩西五经“中有针对移民的内容,“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的地上和你同住,不可欺负他。寄居在你们那里的外人,你们要看他如本地人,并要爱他如己,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作过寄居的“。
针对残障人的内容,“不可咒骂聋子,也不可将绊脚石放在盲人面前“。
针对邻居的内容,“不可欺压你的邻舍,也不可偷盗。雇工的工钱不可在你那里过夜,留到早晨”。
针对穷人和寄居者的内容,“不可摘尽葡萄园的葡萄,也不可拾取葡萄园中掉落的葡萄,要把它们留给穷人和寄居的”。
对待公平既不可袒护富人也不可袒护穷人,“你们审判的时候,不可不公正;不可偏护贫穷人,也不可看重有权势人的脸,总要公平审判你的邻舍”。
对女儿,“不可侮辱你的女儿,使她沦为娼妓”。
对老人,“在白发的人面前,你要站起来,要尊敬老人“……
这样的教训在《旧约》中还很多,还有一本叫做“箴言”的书卷全部都在讲这些。宏大的帝国叙事是不会在意这些伦理问题的,但在以色列人流散他乡的生涯中,正确的伦理观是存活下去的必要条件。没有正确的伦理观维系家庭和社区的健康发展,人家还没来消灭你,你们自己就把自己给干死了。
所以,根据这三点观察,你应该可以看到,以色列在历史的反思中凝练出来的“民族意识形态”,与今天的“锡安意识形态”有多么不同,应该说是背道而驰也不为过。
以色列的历史是站在一个民族失败的经验中的回溯性写作。《旧约》并不是由胜利者书写的,而是由失败者书写的。
以色列在历史中并非没有获得过军事上的胜利,比如Mesha石碑描述了以色列王暗利曾经压制和奴役摩亚人很长时间。还比如著名的马加比起义,建立了长达一世纪的哈斯蒙尼王朝。
但这些军事胜利的经验都没有被纳入到最核心的宗教典籍中。
为什么?
因为以色列真正认清了一个弱小民族获得长期生存和发展所能采取的最有效的姿态和策略——那就是抛弃军事上的对抗,转而在文化和信仰的传承中保存自己的民族性并寻求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自己功用的机会。
因此,《旧约》叙事是反乌托邦的,是批判、否定和解构人所构建的美丽新世界的。这是一个“民族叙事”超越“国家叙事”的典范。
在一次次失败和亡国的经历中,以色列学会了民族续存的最重要的功课,虽然帝国征服带来国家的消亡,却诞生了一个没有军队和圣殿的以色列民族。
锡安的“国家”意识形态
锡安的“国家”意识形态是和以色列的“民族”意识形态背道而驰的。
19世纪末欧洲特别是东欧的排犹政策让很多以色列人对“民族超越国家”的意识形态发生了动摇。18、19世纪也是欧洲国家意识形态迅速发展的阶段。
过去,很多民族都未必有自己的国家。但经过欧洲几百年的打打杀杀,再伴随着资本主义和人权意识的兴起,民族-主权国家的概念开始成为欧洲各诸侯国追求的目标。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欧洲各地纷纷依照自己的民族意愿开始建国并宣告主权的同时,它们马上就跑到那些还没有宣告主权的地方瓜分、掠夺人家的财产和土地。
还没宣告,或还没按着你的方式宣告,可不代表人家在自己的土地上就没主权啊!更不代表那就是你可以随便拿走的啊!
这就好像你总不能就因为把自己养的猪都贴上小贴纸,就跑到人家那儿把没贴贴纸的猪抢过来说成是自己的吧?
口口声声提倡人权却蓄奴、捍卫主权却跑去殖民,说白了都是混蛋逻辑、强盗行径。
这里要驳斥一下以英国托管为二战后分割土地的法理依据的观点。事实上所谓的托管制度完全是殖民主义的产物,它从一开始就是不合理的,根本不能用来作为以色列建国的法理依据。
巴勒斯坦这块土地是谁拥有的?
当然是当时住在巴勒斯坦这块土地上的人拥有!
有一些为以色列背书的人说以色列建国的时候没有“巴勒斯坦人”,那土地上生活了上千年的不是人吗?这种观点是完全内化了殖民主义的思维逻辑,这和美国人说北美土地上没有人、欧洲人说巴勒斯坦是land without people的强盗逻辑完全一致,都是不把人当人看的殖民者心态。
巴勒斯坦的主权归巴勒斯坦土地上的人所有。奥斯曼帝国瓦解以后,巴勒斯坦人理应依照自己的民族意愿建立自己的国家,而巴勒斯坦居民90%以上是阿拉伯人,那么正如欧洲的日耳曼人、高卢人、伊比利亚人依照自己的民族建立自己的国家一样,阿拉伯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本是顺理成章。
然而众所周知的是,巴黎和会上列强瓜分了亚非拉的土地。
他们把山东给了日本,把阿拉伯土地给了英国和法国。
这是我们自己也经历过的羞辱。我们自己经历了被列强瓜分,经历了五四运动,今天居然有中国学者为英国托管巴勒斯坦背书!真是可悲可笑!
而英法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更卑鄙的是什么呢?是英国在一战中和阿拉伯人协定,阿拉伯人参与推翻奥斯曼,便可以获得独立[3] [4]。但不久之后,英国便许诺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建立民族家园[5],与法国秘密谋划瓜分阿拉伯人的土地[6]。

这张图,绿色的就是阿拉伯人原本要建立的阿拉伯国,紫色是被英国许诺给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家的东西凭什么你来许诺?!)。注意,紫色是包含在绿色范围之内的。
巴黎和会最后的结果,是绿色的区域全被英法瓜分。叙利亚、安那托利亚南部、伊拉克的摩苏尔地区成为法国的势力范围。叙利亚南部和伊拉克大部份地区成为英国势力范围。英国也由此获得了伊拉克石油以及巴勒斯坦直至苏伊士运河的运输要道。
而阿拉伯人的土地呢,被分割的七零八落。今天这些阿拉伯国家,也根本不是像欧洲国家那样建立在民族自觉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英法国家人为划分的势力范围基础上。
法国势力范围内的叙利亚地区之后分为独立的黎巴嫩、叙利亚。英国势力范围则在之后独立为伊拉克、科威特等国家。而巴勒斯坦地区,也成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不断冲突和角力的地区。
这才是中东地区冲突不断的历史根源。
根本就不是什么阿拉伯人好斗,穆斯林人好战,犹太人和以色列人世代为仇。老实说,19世纪以前,整个欧洲比亚非拉地区兵荒马乱的多。而直到英法瓜分中东之前,犹太人、阿拉伯人、波斯人大多数时候是和平共处、相安无事的。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仇,根本就不是以撒和以实玛利的仇,《旧约》和《可兰经》里这俩兄弟没有任何世仇,倒是以撒自己的儿子雅各和以扫打个不停。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历史上也没什么深刻的仇怨,打的你死我活的是基督徒和穆斯林,排犹最厉害的是欧洲啊。
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仇,实质上是阿拉伯人和欺骗、掠夺他们土地的西方列强的仇。
而犹太人回到巴勒斯坦推行锡安复国主义,只有在英国成功背刺阿拉伯人、分割中东、抢夺巴勒斯坦的大背景下才有实现的可能,这从一开始就是深深植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完全脱离了《旧约》和拉比们一直信奉的“民族大于国家、民权大于君权”的民族叙事。
另一条路……
实际上,以色列是可以不选择依赖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扶持回归家园这条路径的。
犹太人自己也一度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受害者。他们被帝国征服,被殖民者驱至万邦,他们自己就经历了失去家园和寄人篱下的痛苦,自己就是从排挤和屠杀中走出来的民族。
当然,大屠杀成了很多犹太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们渴望有一个自己的国家,不再受驱赶,不再被死亡威胁,可以安居乐业,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
我想,这样的诉求没有人会不理解,会反对。事实上,在二战后,全世界都是同情犹太人的,特别是在欧洲。其实那个时候即便以色列不建国,系统性压迫犹太人的历史也不会再重演了。
之后的发展趋势我们也看到了,前殖民地纷纷独立,人权和主权成为主流价值,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种族歧视不再理所当然,全球化把全球南方和全球北方日益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虽然时有反复,但大体上,人类是在往更公义、更和平、更强调合作与发展的方向走了。
在这新的世界格局和历史时期中,一方面,犹太人不用再担心大规模的排挤和逼迫。另一方面,企图复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野心路径也将无论如何再也行不通了。
真的很遗憾,以色列完全可以不必搭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末班车的。
如果以色列1948年没有建国,那么巴勒斯坦应该建立了阿拉伯政权,或许是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或许是叙利亚、黎巴嫩或约旦的一部分。那么犹太人和阿拉伯人的矛盾就不会激化,以色列就不需要在本该和平的年代打仗,数百万的巴勒斯坦人就不会流离失所,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就不会生灵涂炭。
再想象的大胆一点,如果以色列没有建国,或许阿拉伯国早先就有了统一的机会,那么接下来整个世界的格局走向就会全然不同。美国在中东就难以像今天这样搅动浑水,阿拉伯人就更有能力捍卫自己主权,就不必借助恐怖主义声张诉求,那么也许911就不会发生,也自然就没有了后续的一系列战争。
当然,这个世界没有“也许”,过去的也已经过去,谁也无法重写历史。
但无论如何,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两百年前的世界了。
今天的全球南方经历了殖民主义解体、民族独立、政权更替和一系列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动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觉醒和意识来对待强权、霸权和侵略。最近的联合国大会的决议表态就证明了这一点,全世界越来越高涨的声援巴勒斯坦的运动也证明了这一点。和阿拉伯、穆斯林没有一点关系的南美国家首先站出来和以色列断交也证明了这一点。
这不是反以色列,更不是反犹,这是反西方霸权,反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死灰复燃。反对的是美国主导的对抗和分裂,发达国家长年累月对发展中国家的军事恫吓和资源剥削。
而且,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那就是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的力量此消彼长,过去手无寸铁的孩子逐渐长成,以色列在今天是再也无法复制殖民主义的了。
——他们老了,而我们还年轻。
参考
1. 具体分析可见前两篇文章。
2. 根据旧约,“以色列“和”犹大”最初为大卫统一建立,后分裂为北国和南国。但现在考古学一直没有足够证据证明统一时期真正存在过。
3. 侯赛因-马克马洪协定
4. https://www.un.org/unispal/document/auto-insert-199699/
5. 贝尔福宣言
6. 赛克斯-皮科协定